2025年成都車展之后,知乎的朋友邀請我回答了兩個問題,分別是《2025成都車展,電動化與智能化的「內卷」,是否正在重新定義「好車」的標準?你的選車標準是什么?》和《從成都車展來看,燃油車是否已淪為「功能性補充」或「情懷產品」?》
這兩個問題都非常好,也讓我自己突然悟了2025年中國汽車行業的一些共同性問題,以及一些車企在戰略上的選擇。
這兩個問題看上去沒有什么關聯性,但是邏輯思考其實是連貫的。首先是要明白智能化和電動化的內卷所帶來的產品趨同和體驗一致化,然后再去思考車企要如何跳出這種內卷,最后會發現用戶差異化體驗更多源于于驅動形式,要在電動車時代做出差異化那就是去往燃油車的方向,這也就有了增程的崛起。
所以,一輛好車的標準無關于驅動形式,也無關于電動化、智能化,而在于一輛車在某個價位所能夠賦予駕駛者和使用者的情緒價值。最終而言,福特烈馬1966和凌渡L GTS有情緒價值,想來帕里斯帝的2.5T油混也有情緒價值,沃爾沃XC70的情緒價值就和領克不一樣,蔚來和理想也有各自的情緒價值。

當面對拿出真金白銀買車的消費者的時候,車企要給到消費者的必須是獨一無二的價值,這個價值必須是主觀判斷的,而不是說競品有的我也有、我的參數比競品強,那消費者憑什么聽你的?
01
內卷不會停,除非你跳出來
怎么理解汽車行業電動化與智能化的內卷呢?我認為本質上就是PC時代和智能手機時代的重演。
PC時代同樣是產品同質化嚴重,大家都學著Wintel聯盟,Inter Inside模式就是現在的HI模式,車輛上的智能座艙和智駕都是高度一一致化,而大家比拼的是外殼造型、CPU首發、又或者是高性價比。“高性價比”這個模式很有意思,比如一開始的戴爾模式,戴爾提供了大量的標準化設計、通過規模降低成本,然后再發展出家用、商用、學生機等不同產品線,同時用直銷模式打破了惠普、康柏這些巨頭的高溢價。
當然,在品牌溢價之下也有所謂的DIY模式,電腦城的零部件供應商把零部件直接給到消費者或者裝機點,使用盜版軟件,最后降低成本,從而實現銷售。而后來出現了神舟電腦,直接配置拉滿,首發最好的芯片、最高的規格,但是細節做工問題不少,也沒有很好的質保,可是消費者會被價格打動。
后來因為筆記本電腦的普及,PC時代落幕,因為大家始終發現單純追求高性價比和自助裝機實在太麻煩了,大廠家撇出溢價之后帶來的體驗高度一致化,大家選擇的是其實就是品牌和體驗而已。
智能手機也是同樣的問題,區別就是手機廠商會在安卓開源基礎上做自己的換殼系統,以前還叫UI,后來直接叫系統了。手機的性能受制于高通、索尼提供的元器件,真正的差異化賣點非常少。再到后來,手機廠商開始意識到需要差異化,這種差異化的本質是需要刨除參數的影響,而是把“主觀感受”作為賣點。

因此手機廠商就衍生出了手機攝影作為旗艦機的差異化,你有徠卡我有蔡司,你有高像素我有人像,同時還把系統生態做成了差異化,你的手機平板電腦可以互聯,我就來兼容蘋果和兄弟機。還有一個差異化賣點就是折疊屏,你的折疊屏性能好,我的折疊屏犧牲性能做輕薄,而他就做三折疊。
當然,不管是電腦還是手機,最后要跳出內卷的方式其實是學蘋果:軟硬件一體化。我的自研芯片可以跳出公版設計,我的SoC可以優化自己的系統和生態,我自研的NPU可以拍照更好、AI更快。
看懂這些,再回到汽車行業,你會發現現在汽車行業對電動化和智能化的內卷其實像極了當年的PC和手機時代。你用英偉達的智駕芯片,我用高通的芯片,你用華為、我用Momenta、地平線。大家本質上不會有太大差別,研發能力主要靠供應商。這也就有了蔚來、理想、小鵬、Momenta都開始做自己的AI加速芯片,本質上就是想跳出這樣的內卷,從而建立自己的生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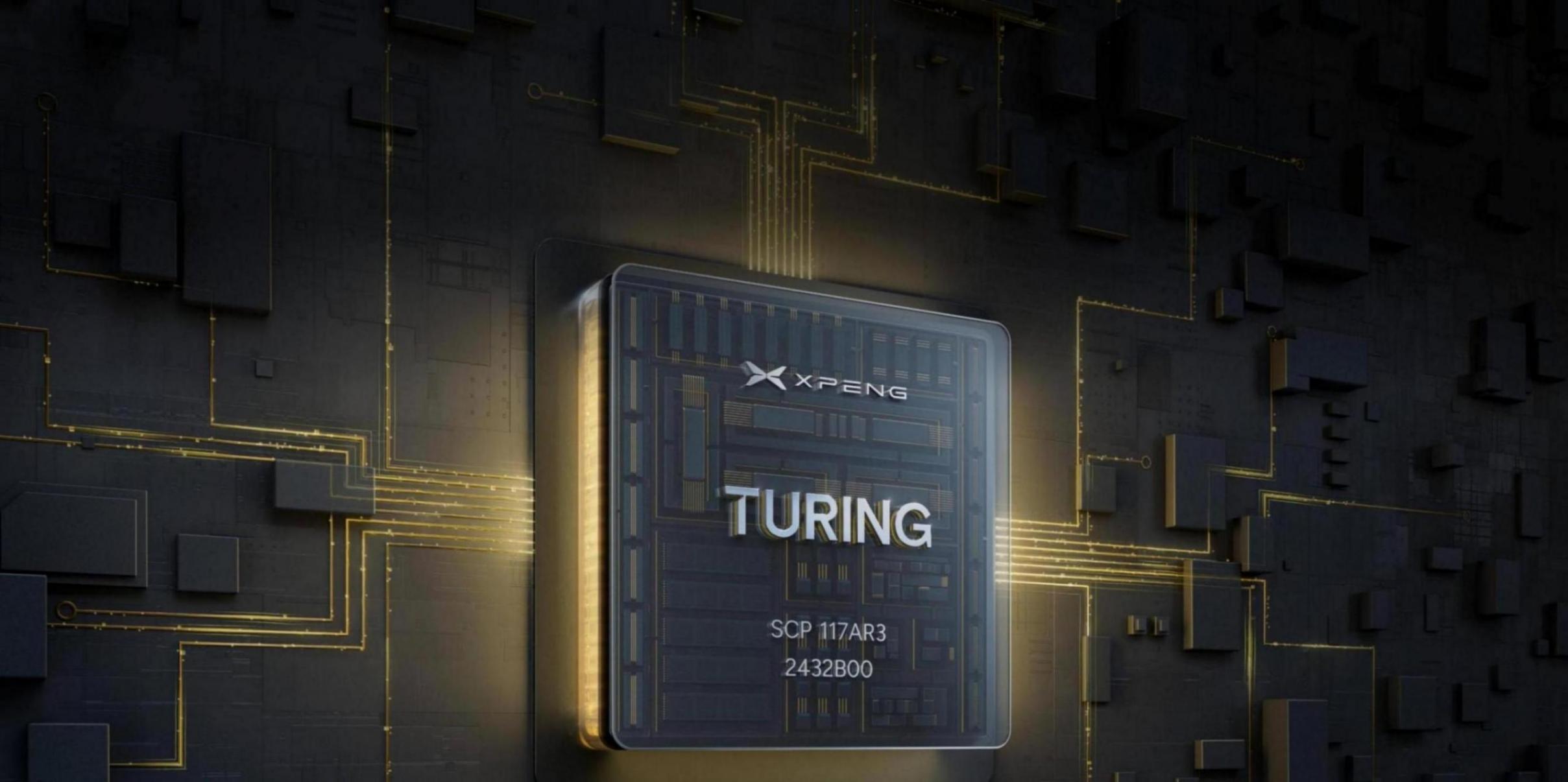
但是大家都說學蘋果,可是軟硬件一體的難度,以及發展速度都比想象中更難。蔚來做出了神璣、小鵬做出了圖靈,實際收益還沒有反映到性能上,而英偉達的Thor-U和高通8397依然是被視作行業最優選擇。這就好像在AI時代,蘋果A系列芯片押注了CNN神經網絡,確實可以優化自己的系統,但是現在英偉達、Google們跑去支持Transformer,蘋果在AI領域就很尷尬了。只是蘋果有豐厚的現金流可以再搞AI專用芯片,而汽車企業就不敢這么賭了。
所以,電動化和智能化的內卷肯定在重新定義“好車”——算力高就是好、智駕強就是好、電機強就是好——但是這種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本質上沒有拉開差距。
那么什么才能拉開差距呢?就是我之前說的,本質上還是品牌價值、情緒價值,一款車的產品力強不是說你的產品參數能夠有多強,而是要給到用戶一種“主觀”價值的判斷,就好像是手機的攝影、手機的生態。
所以,汽車行業在這種一致化趨同的前提下,車企要做的好車不是說參數碾壓、性能碾壓,而是要讓用戶能夠有一種自我主觀判斷的“好車”。
這就讓我想起了富士中畫幅和哈蘇中畫幅,兩個相機都是1億像素CMOS,但是哈蘇X2D2可以賣5萬多,富士只能賣3萬多,這個一兩萬元的差距其實是哈蘇HNCS(哈蘇自然色彩解決方案)。大家認為HNCS的好,是超越參數的,但本質上這只是一個主觀判斷。
因此,未來汽車市場的好,可能燃油車是“情懷”、“情緒價值”,電動車是“智駕”、“體驗”,但無論如何你都需要有一個別人無法超越和跨越的護城河,否則單純的“好”就沒有意義。
02
好車的標準是不被時代左右
這次成都車展我選出了自己喜歡的六款車型,分別為:沃爾沃 XC70、捷途縱橫 G700、上汽凌渡L 380TSI、奇瑞風云T11、烈馬1966、現代全新帕里斯帝。可以看出來,這里面凌渡L、烈馬1966、帕里斯帝算是純燃油車,而福特縱橫G700、烈馬、凌渡L都算是情懷價值很高的產品。

所以我自己的一個結論是,當中國車市進入到2025年,燃油車顯然能夠提供更高的情緒價值。而這背后的原因其實不是說燃油車的產品定義更復古,更多原因是因為燃油車會讓消費者有更多差異化選擇,比如更有樂趣、可以更多考慮戶外使用、有更多的創新價值。
因此,“對燃油車有情懷”這件事情,其實首先是基于“這是一輛燃油車”。
比如凌渡L做GTS,搭載一臺2.0T發動機、賣13.99萬元,它的吸引力在于燃油A級車很難有高功率發動機,可是電動車動輒200kW的電機,大家都可以輕松買到。同時,燃油車車身重量更輕,搭配一臺2.0T高功率發動機會有更輕快的駕駛樂趣。而電動車即便是有200kW的大電機,但是卻有著更重的車身、更笨重的操控,因此并不被喜歡。這時候,當A級燃油性能車和電動車一個價位的時候,就顯得很有“價值感”了。

再比如我們看烈馬1966。這是烈馬推出的一個復古版本,之所以叫1966是因為烈馬誕生于1966年,這輛車采用了初代烈馬的很多設計元素,比如白色的進氣格柵、白色的復古輪轂、欠飽和度的車身顏色,一切顯得粗糙而富有精神價值,容易想起荒漠馳騁的感覺。
但是你如果換成電動車,很顯然電動車天然沒有這種關聯,一是無法那么快速建立起和六十年前的聯系、二是消費者也不認為電動化是一種先鋒的體驗,而非烈馬那種戶外野性。所以烈馬就算把自己的新能源版本做這種復古改造,也不能喚起消費者對烈馬的熱情。

同樣,看縱橫G700、現代帕里斯帝這些方盒子造型的產品,本質上都是因為他們有發動機,所以才敢不顧風阻、不顧能耗,把車輛的造型和需求做得更極致。盡管燃油車可能沒有那么“智能”、“先進”,但是對于很多消費者來說,選擇車輛的出發點還是移動出行和大空間乘坐,是不是電動車反而不是第一個關鍵要素。

實際上,現在車企對電動車的想象力越來越匱乏,幾乎就被禁錮在城市通勤、闔家歡樂兩個維度。因為電池的局限,電動車需要追求低風阻、追求更圓潤的表面、需要妥協第三排空間、需要把車做得更柔美、動力輸出必須克制、做不了跑車。你當然可以選擇不做,比如iCAR V23那樣,最后只能有小電機、短續航,又或者像小米SU7 Ultra一樣追求運動性的同時放棄能耗。

所以,最終我們會發現,選擇電車就意味著放棄樂趣、個性和生活的肆意,而選擇燃油車,你卻可以獲得你想要的一切,唯一的問題是你需要額外付出10%,然后交出所謂的智能、智駕。
這時候你再看這個話題,你會發現燃油車之所以是情懷產品,完全是因為你放棄了自我的選擇,燃油車之所以是功能性補充,是因為你把互聯網當成生活中一秒都不能離開的東西。所以,在成都車展上,你看待燃油車是補充、是情懷,從另一個角度在于你選擇了所謂的電動化生活而放棄了自我選擇的意識。
當然,如果從最終結局來說,加上油箱或許是一個自我意識的覺醒,也是脫離電池局限的開始。當你不再為能耗而焦慮的時候,情懷也就回來了。
